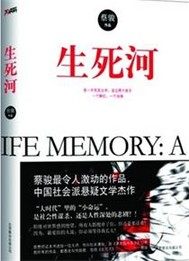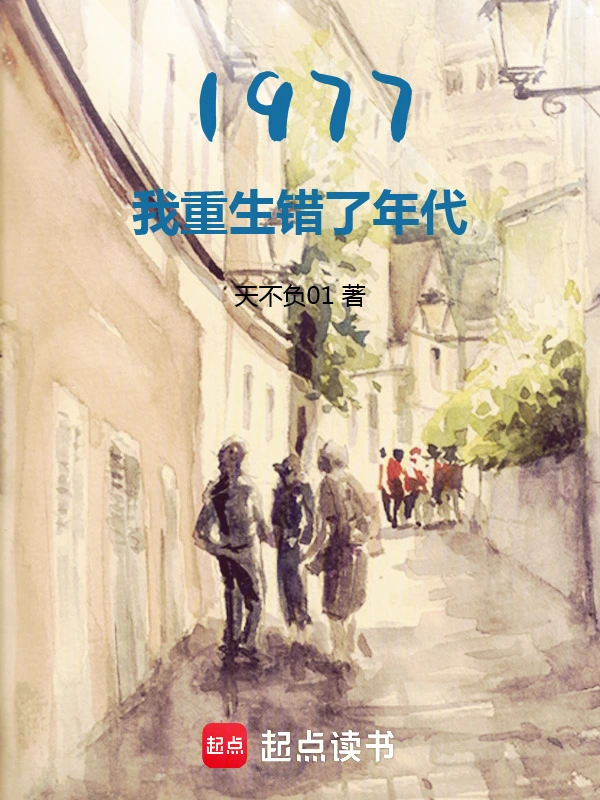歡快的 小說 生死河 第十六章 品读
漫畫–綠燈俠第二季–绿灯侠第二季
2011年6月19日,毫無二致時辰。
錯嫁王爺巧成妃
尹玉到滿清普高對面的空中客車站,穿顧影自憐反革命家居服,白色掛包掛在後面,短出出頭髮更顯氣概不凡,咋樣也袒護不止血氣方剛佳的相貌。
十六歲的司望在等着她。
尹玉高閒庭信步地湊攏:“喂,你兒子!決不會是專程望我的吧?測試安了?”
“還沾邊兒,着守候收效昭示,企望能落到北魏高級中學的保障線,回到這裡做你的同學,你呢?”
他斜倚在路牌幹,敞的衣領吹着風,引來經過的自費生敗子回頭。
邪帝狂妃鬼王
“前幾天會考剛殆盡,我想我要去**了。”
“啊?你安沒跟我說?”
“我投考了**大學,既議定了高考。”行將背井離鄉的她,櫛着頭上的鬚髮,“我適應合此間的高校,怕是即使如此考進了華東師大文學院,長足也會被強制退學的,還自愧弗如去**,烈性少些牽制。”
“恁,其後就見不到你了?”
“我會常事回去看你的!”
她拍着司望的肩膀,同樣靠在海報液氧箱上,不論是殘陽灑在臉龐。有的是剛出旋轉門的高中生,如林衣裙子的受看三好生,向他倆投來爲奇的目光,懷疑這個出了名的假少年兒童,怎會跟認識的小帥哥在同臺?
出人意料,他低聲提議個事故:“你去過魔女區嗎?”
“吝嗇!我語你,早先這近水樓臺都是塋。阮玲玉的墓就在魔女區越軌。她是香港人,死後葬入沂源皇陵,其時叫聯義別墅,造得異乎尋常蓬蓽增輝,簡直是一座免職莊園。進門後經由一座螞蟻橋,有點滴赤縣神州古典建,局部坐棺,組成部分贍養神佛。墳墓幾近石砌,造得古拙,還有石桌石凳石馬石羊,線圈丘後包着一圈崖壁,超羣的陽面蒲團椅式大墓。一些仿造帝王墳丘,竟有暗道暢行無阻西宮,幸虧是明清,不然一度盡數抄斬了。相對而言,阮玲玉的丘墓極端方巾氣,墓碑也就一米多高,金屬陶瓷照上是她最先的莞爾。‘**’時整片墓地被拆光,造起了學校與廠,那些小康之家的防地,皆殘骸天南地北消逝了!對了,東晉國學的天文館,實際上是早年海瑞墓建設的局部,專門供奉屍體靈位的廟舍。”
尹玉說得粗騰達,這麼些紅男綠女生早戀都在這文學館裡,卻不知曾是擺滿靈牌的經堂……
“你魯魚亥豕說哪裡死大嗎?”
“殭屍?那可是太正常化的事了,有誰人生上來決不會死?呵呵,所以我最不堪設想的縱厚葬,死後燒成爐灰往海里一撒才齊潔!
“你怎麼對阮玲玉的墓葬那麼稔熟?不過親身經驗的媚顏能這樣,你謬誤說‘**’時拆光了嗎?你又是怎麼目的?莫不是你參與過她的閱兵式?”
“毋庸置疑。”
十八歲的貧困生乾脆利落地回話,倒是讓司望莫名了,停歇稍頃又追思怎麼着:“再問一下關鍵——你說在1983年,上輩子的你住在困路,迎面房屋裡生了一樁謀殺案,截至當初一如既往蒼涼?”
“名特優新,干卿底事?”
風乍起,吹皺一池春水。
“你還忘記一期伢兒嗎?那時候十三歲,他的外祖母是廝役,在你住過的那棟房屋窖。”
“雲姨的外孫子?”
舊愛的秘密,前夫離婚吧! 小說
“說得着。”
“是啊,雲姨是我的奴僕——我可以是哪樣闊老,單獨八十多歲全身食管癌,國家爲續我的冤與災害,經過常委會找來雲姨照顧我的過日子食宿。她的身段凌駕健康人的好,嗬喲髒活累活都老練。她唯有一個半邊天,幾年前被人害死了,留給個孩童孤零零。我同病相憐雲姨與她的外孫,就收留他們住在窖裡。我早忘了壞女性的諱,只記憶他讀很好,從此以後竟然考進了着重高中。”
司望榜上無名地聽着這整個,表情略略詭異,尹玉跟手往下說:“我看着他從小學徒變成實習生,一去不返大人包管還沒學壞。我常看齊他在地窖,憑着一盞灰濛濛的場記作業。他很愛看書,我就貸出過他一套侈談本的《聊齋志異》。寐旅途的親骨肉們,沒人答應跟他旅伴玩,偶爾頻頻赤膊上陣也會爆發成鬥,歸結他城市被打得骨折。而他止個公僕的外孫,哪敢挑釁去復仇?雲姨很迷信,總顧忌這孩面目欠佳,大概將來的命不長。”
這段話卻讓人尤其堵,他飛快變化了話題:“這兩天我狂看顛撲不破點的書,我想常有不生活怎改編轉世,惟一對人會從墜地的功夫起,就備一種不凡力,能領導其他已經殞命的人的整個記憶。”
尹玉的神情稍許一變,泛前輩非常的懷疑:“好吧,縱我兼而有之一個男子的回憶,一下出生於1900年的漢的記憶。”
“1900年?八國聯軍打進北京那年?”
“是,光緒二十六年,庚子變。”
“你還牢記那一年的事?”
“委託啊,兄弟,那一年我剛落草嘛!”她看着邊塞早霞漸漸穩中有升,南明路被金色餘年包圍,按捺不住閉着雙眼吟出一句,“種桃方士歸何方,前度劉郎今又來。”
“這句詩好耳熟啊!讓我思忖?”
“後唐劉義慶的《幽明錄》記載,秦代劉晨、阮肇二人天堂太白山,如夜來香源銘肌鏤骨溪澗,欣逢兩位少女,迎他們深中造訪。劉、阮二郎如入瑤池,‘至暮,令各就一帳宿,女往就之,言聲清婉,好心人忘憂’。他們與淑女朝夕共處十五日,終竟忖量鄉土歸去。待到兩人下山,莊子早就面目一新,淡去一番鄉黨解析,工夫已流逝到了晉朝,距他倆進山往日二百常年累月,昔時的後嗣已到第二十代,‘傳聞上世入山,迷不得歸。至晉太元八年,忽復去,不知何所’。”
“聽起牀真像是和田•歐文筆下的故事。”
尹玉拍了拍他的肩胛:“小崽子,還到底老漢骨肉相連!唐宋劉禹錫再三被貶邊陲,在他第二次返回延邊的玄都觀,衆寡懸殊連篇悽婉,才感慨萬端‘前度劉郎今又來’。”
“你亦然再作馮婦?”看她歷演不衰沒酬對,司望小徑歉了,“我太唐突了吧?”
“二十世紀,以癸年發端,我生在一番破碎的斯文家,幸有做生意的堂叔贊助幹才離鄉習。1919年5月4日,我就在賽場上,火燒趙家樓也有我一份。沒想到伯仲年,我去了尼日利亞留洋——對了,你看過蒼井空嗎?”看他面露酒色,尹玉舞弄一笑了之,“現在我已是婦道身,對此根本不志趣。可在我的上輩子,卻與巴西聯邦共和國女兒結過良緣,在長崎讀書時,有個叫安娜的婦與我愛得充分,末尾竟爲我殉情而死。我記不得她的原名了,她是天主教徒,只記憶教名。”